


第一届甘肃散文八骏 陈宝全
陈宝全,甘肃省静宁县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甘肃省作协理事、平凉市作协主席,静宁县文联主席,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散见于《飞天》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文学港》《草原》《黄河文学》《朔方》等纯文学刊物。获第四届甘肃黄河文学奖、崆峒文艺奖。著有诗集《看见》《心生繁花》《等于鸟鸣》,散文集《被一颗苹果喜欢过》。

【创作感言】
飞翔的鋬笼
父亲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匠人,他会修房子、做家具、打磨子、盘炕……在这些耍手艺的活计中,编鋬笼的手艺让我曾一度非常着迷。
多数时候,父亲选择下雨天编,我不知道这是他的习惯,还是雨天榆树枝会变得更加柔软,也或者是只有这样的天气他才能安心做这件事。当我从黎明的酣睡中醒来,看见榆树枝在他手指上舞蹈,就懒得起床,静静地趴在被窝里,看着他打底、编帮,插入一根又一根榆树枝,扭来扭去。差不多一个早上就能编好一只鋬笼。
我喜欢看着父亲编鋬笼,但从来没打算自己动手编一只。父亲说,打底很关键,收口最显手艺。我感觉打底就像文章的开头,而收口像文章的结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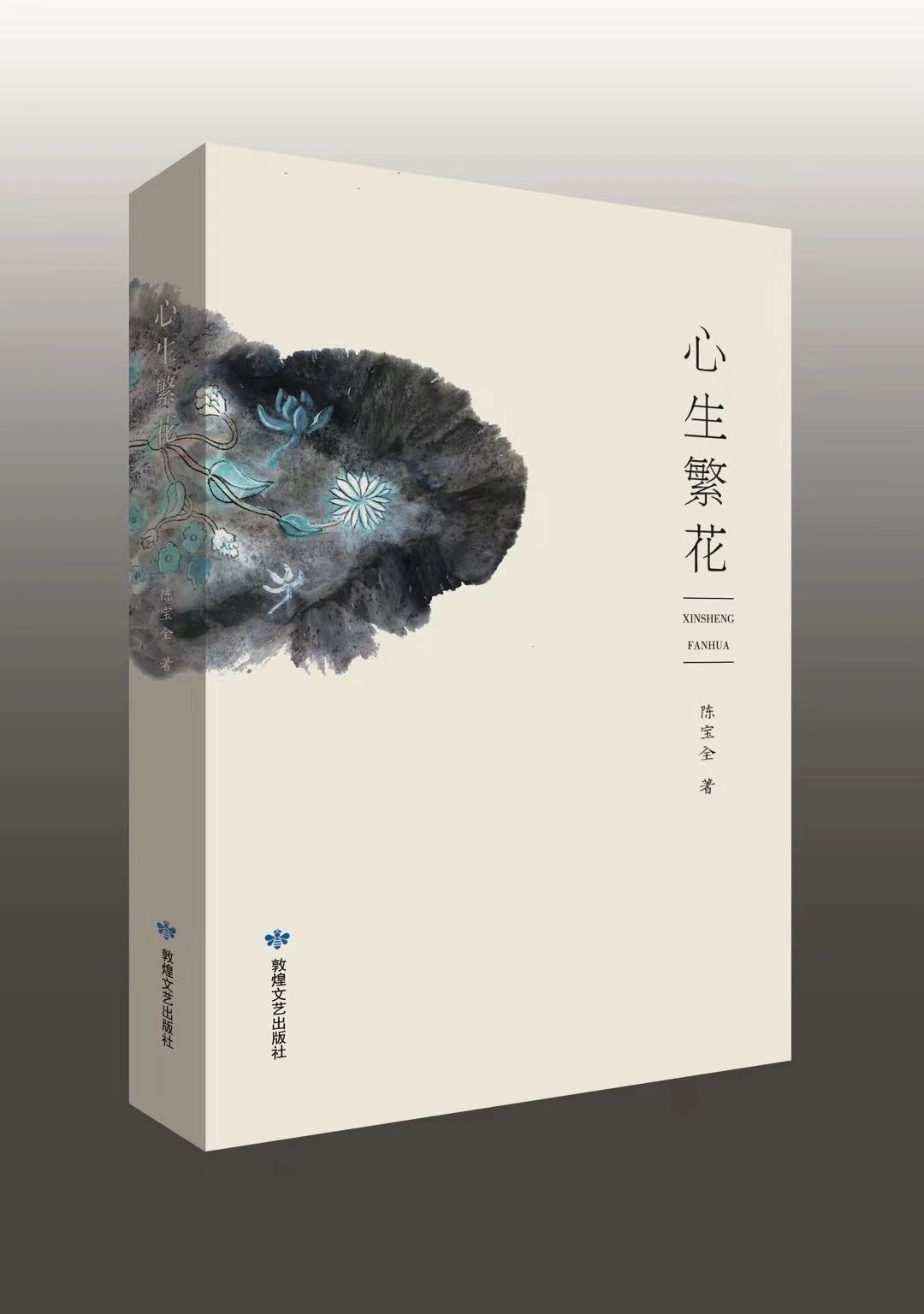
那时,我还在上学,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。六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《家乡的雪》意外变成了铅字,文学的种子就这样在心里发芽了。从此便投入极大的热情,迷恋那些分行、或长或短的句子,并且大言不惭地说它们是诗。
参加工作后,我偶尔还会写下一些长短不一的句子,仅仅是偶尔。也有一些小东西在报刊,甚至文学杂志上发表,让我兴奋不已。这种热情,并非天生,也与其他方面的需求有关。走着走着,许多梦想都被现实的激流冲淡了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想,喜欢什么,不喜欢什么,似乎不需要任何理由。那些消失的也不是我不喜欢的,还在坚持的必定是让我难以割舍的。
再后来,工作、育儿,生活的担子似乎重了起来。文学的种子那时候应该破土而出了,但还没有舒枝展叶,呈现出生命的力量。我的父亲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,离开农村的家,来城里和我一起生活,帮助我料理杂乱无章的日常。他不再施展才华,为我们家编鋬笼。我仍然会装模作样地写一些结结巴巴的短句,并试图用它们打通生活与精神的通道。它们就像蒿草一样,从我的身体里长出来。
孩子们一天天长大,有父亲和母亲的帮助,加上工作变动,我有着大把的闲散时光。大概是2012年春天,我真正狠下心来,开始疯狂写作,仍然以诗歌为主,先后出版了三本诗集,给我的生活营造出了一种梦幻的氛围。不觉间,时间已经把我捏成了中年的模样,对生活多了一些感悟和成熟的认知。2019年,父亲在果园里砍掉那些老掉的苹果树,深深地触动了我。而诗歌表达后剩下的部分无处安放,于是,我决定以散文的方式来书写。那一年,我创作并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被一颗苹果喜欢过》。

在这本散文集出版的那一年冬天,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我将逃离的目光再度投向我生活过的那片土地,躬下身子,听一株小麦抽穗的声音、看一只虫子勤快地讨生活、和一片久违了的谷子打招呼、用心体会一株玉米发育后的疼痛、和一个即将远行的苹果谈起未来……我希望我的文字带着泥土的芬芳,也力求我的散文有着诗意的存在。
没有想到的是,我把一件写作活坚持了这么多年,还乐此不疲!于我,文学也便成了一种恩赐,成了一种日常习惯,也成了一种难以戒掉的瘾。细想,我试图逃脱的生活以另一副面孔出现在我的生命中,是的,我不是一个像父亲那样用榆树枝编鋬笼的匠人,却是用一支笔来编织,准确地说是用语言编织“鋬笼”的匠人。语言就是我手中的榆树枝。

写作的时候,我总会联想到编鋬笼这门手艺——以打好的底为中心,一圈一圈、一点一点地编织,纵横交错,疏密有度。并固执地认为好的作品需要精心编织,激励想象,激励认知。当然,我更注重文本是否杰出,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,并一下子记住了,那就是: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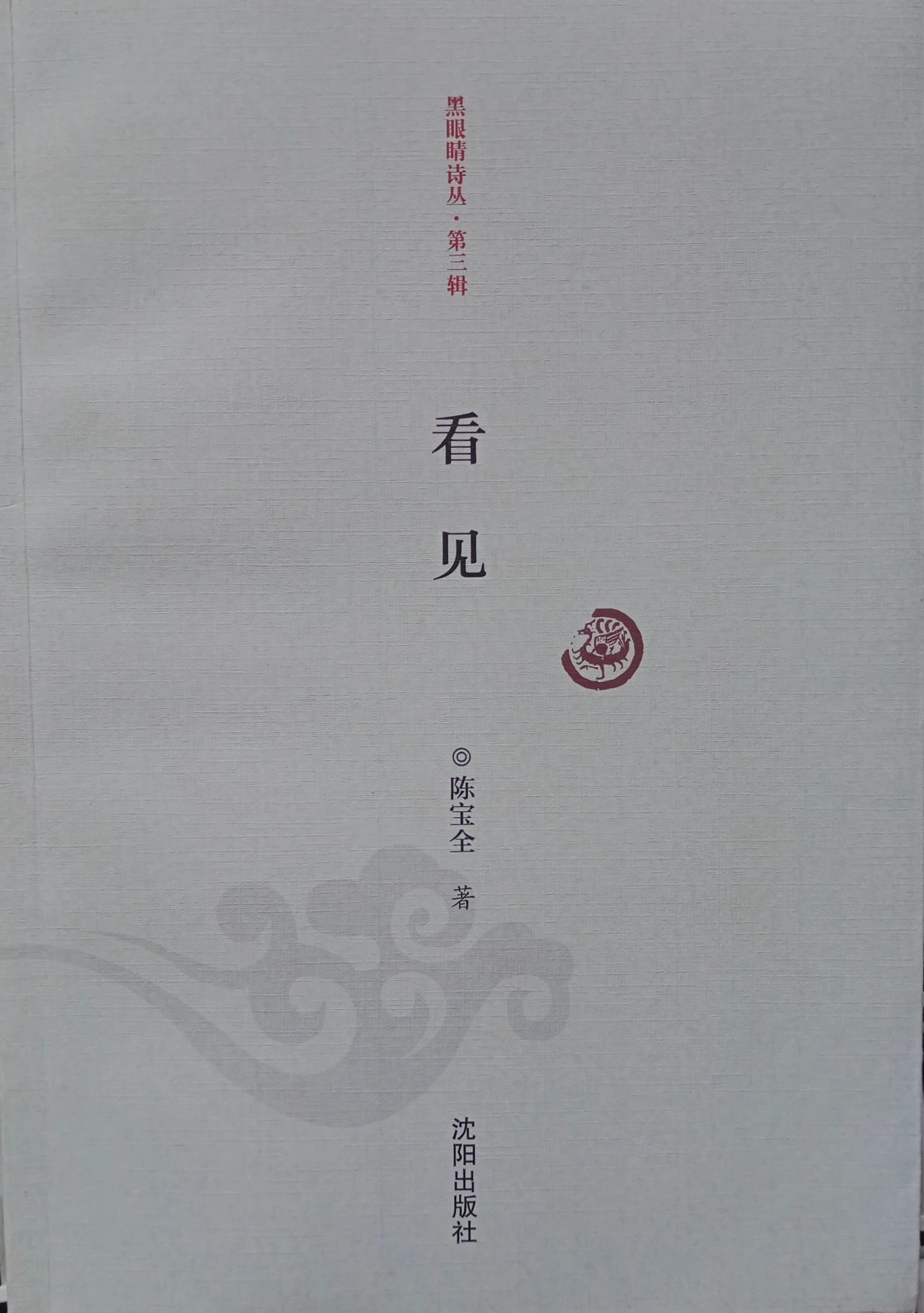
父亲是编鋬笼的匠人,我大概也算。只是,父亲编的鋬笼是用来装东西的,而我用语言编织的“鋬笼”,它长着翅膀,可以飞向高处,盛得了月光,装得下星辰。我们父子编的是两种不同的“鋬笼”,如果你看到我编的,真是我的庆幸。我,这个文学的“小匠人”还在干着编织的活儿,我渴望编出的每一只“鋬笼”都有飞翔的能力。
供稿:甘肃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