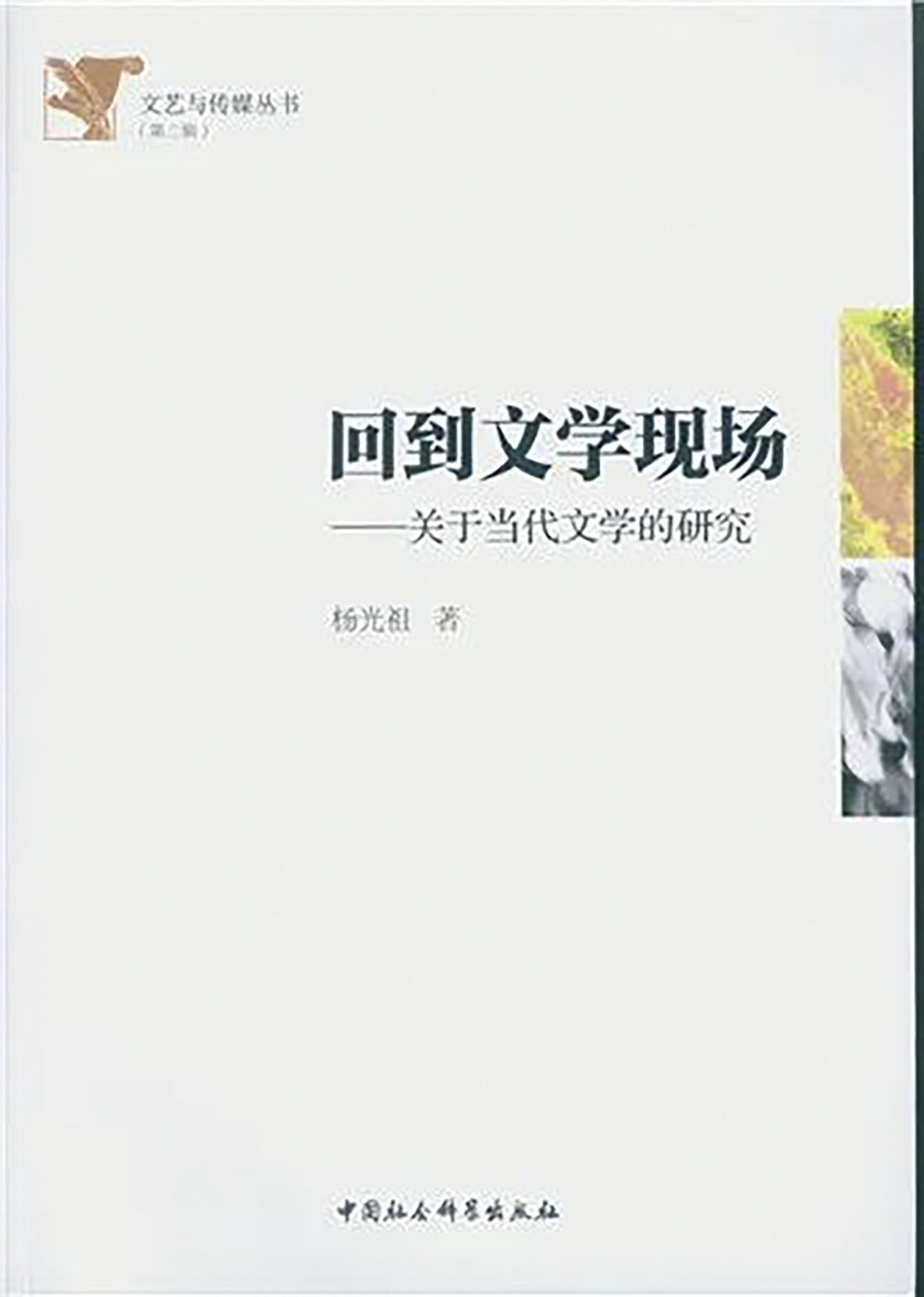杨光祖:批评的思想之光
发布时间: 2022-08-02

杨光祖,1969年生,男,汉族,甘肃通渭人,文学评论家,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当代文艺评论中心主任,教授,博士生导师,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,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,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,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教指委委员,甘肃省领军人才,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,甘肃省文史馆研究员,甘肃省第三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,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(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)学员,中国文联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研究班学员。